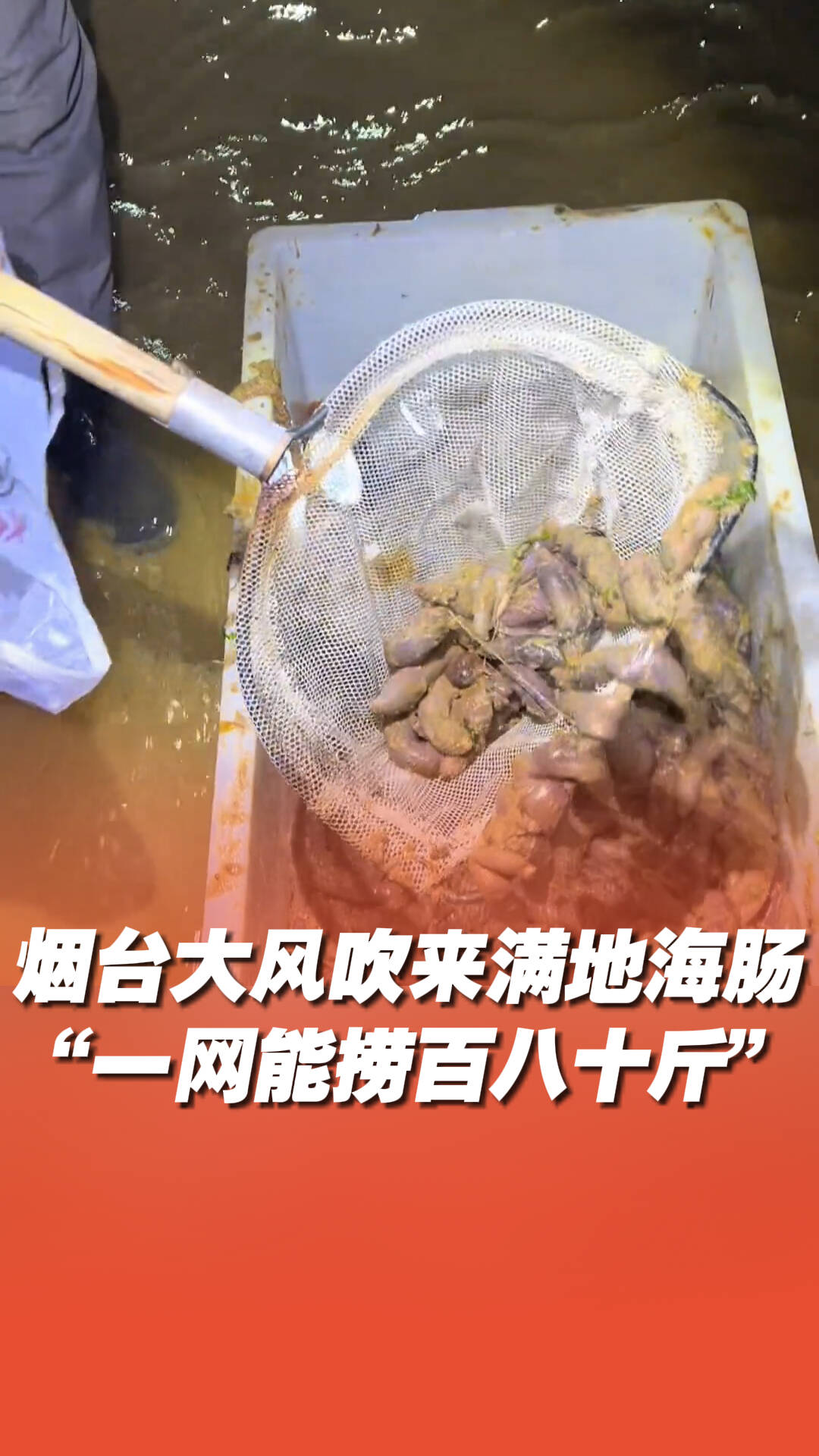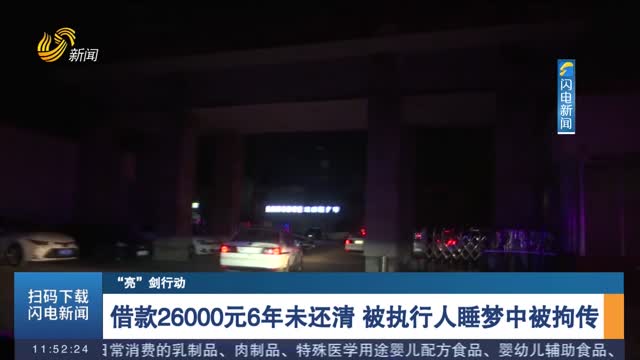被誤解的關中和關中人
來源:檢察日報
2025-03-29 14:58:03
原標題:被誤解的關中和關中人
來源:檢察日報
原標題:被誤解的關中和關中人
來源:檢察日報
何為關中?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四關之中,即是關中。關中南有秦嶺橫亙,北有黃土高原,西是隴山,東是黃河崤函,四周都是天然屏障,這樣的地理條件,既是優勢,亦是弱點。優勢在于“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而弱點則為,若閉關成一統,勢必故步自封,難以為繼。對關中的誤解,多與此相關。
“關中無螃蟹”,是對關中的誤解之一。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五“雜志二”中記載:“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余在陜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干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掛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以親歷者之口,證明關中無螃蟹之可信性,又有“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之趣語。汪曾祺先生曾在文中引用該故事,因此傳播甚廣。對于這樁公案,陳忠實、高亞平等關中作家都曾在文章中予以否定,理由很簡單,親眼見過秦嶺腳下溪流里有螃蟹。事實的確如此,1982年,我參加學校秋游時,曾和同學們在終南山阿姑泉捉了一飯盒螃蟹,雖然個頭很小,只比硬幣大一些,但的確是螃蟹。
“天府之國”專指四川,是對關中的又一誤解。歷史上,最早被稱為“天府”的,其實是關中。《戰國策·卷三》中,蘇秦到秦國游說自己的連橫主張,當面恭維秦惠文王統治的地方是“天府”:“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漢高祖劉邦稱帝后,婁敬勸諫定都長安,諫言得到留侯張良的贊同。據《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說:“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據統計,《史記》和《漢書》中共有六處有“天府”之語,其中五處都是指關中。而稱巴蜀為“天府”,則晚至漢末,《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有“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之語。
關中人保守,亦是對關中的誤解。自周起,關中人就時常走在中華文明進程引領者的位置。“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詩經·大雅·綿》記載了周人始祖古公亶父率部族從豳地遷移至周原,建屋造城,發展農業生產,建立起以地緣關系為主的社會組織。可以說,關中是周取代殷商統一天下的大本營、根據地。
周時遠道遷徙來到關中的還有秦人。最初,秦人在渭河平原最西側的汧水、渭水匯合處給周天子養馬,功績卓著,周天子賜以秦邑,是周的附庸國。秦人長于畜牧,“善御”“善走”。《史記·秦本紀》記載,秦人先祖造父為周穆王駕車遠行,可以“一日千里”。周平王為避犬戎東徙雒邑,因秦人帶兵護送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岐以西,處山河環護的四塞之內,西北要拒犬戎來犯,東有山東諸強國,南是秦巴山區阻隔,秦人所要面對的,既有戰爭危險,更有貧窮閉塞落后之困。輸在起跑線上的秦人不肯坐以待斃,致力于尋找破解之策。“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漫長努力中,秦人不拘一格招賢納士,變法鼎新發憤圖強,至商鞅變法達到高潮,“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斗諸侯”,終于一統天下。
秦統一天下之后,書同文、車同軌,雖二世而亡,卻開創了百代皆行的秦制度,在中華文明進程中留下了極其重要的歷史篇章。在秦人的諸多成就中,交通方面的創新既是成果,又是手段,尤為重要。
秦人偏處西隅,向東是最主要的交通方向。秦人很早就沿境內河流從事水上運輸,輸粟于晉的“泛舟之役”,就是史籍所載規模空前的運輸活動。春秋時期,秦人曾“造舟于河”,并在黃河歷史上修建了第一座常設的浮橋。戰國時,為阻止質于秦的燕太子丹回國,秦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雖未能成功,但秦國橋梁建造技術水平由此可見一斑。水上運輸發達及橋梁建造技術高超,使黃河之于秦人,已不再成為天險。在陸地交通上,秦人在戰國時期修建了函谷關,扼守崤函古道,自此使關中具備了“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的地緣優勢。
向南,秦人征服秦嶺巴山天險,修筑了通往巴蜀的棧道,這是世界交通史上的創舉。秦巴險峻難行,“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秦人創新性采用“鑿孔架木”技術,以“地崩山摧壯士死”的代價,在此間開鑿道路,使“天梯石棧相鉤連”,用千里棧道聯通了兩個“天府之國”,從而改變了與山東強國的實力對比。
向北,秦人“塹山堙谷”,修建了從咸陽直達今日包頭的秦直道,將“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里”的軍事防御體系長城與關中以最短距離連通,是漢代北擊匈奴的重要通道,后世沿用數百年。
“治馳道”,是秦人最具時代特色的交通建設成就。馳道被喻為最早的“國家級高速公路”,據記載,其形制“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設分隔帶,道路整體規模“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同時建立了與之相配套的馳道交通規則。至漢武帝時,馳道幾乎遍達“天下郡國”。馳道制度標準化、網絡化的思維,奠定了中國古代交通體系的基礎,其影響力延續至明清時期。
回望歷史,僅從秦漢交通方面的創新成就,就足以窺得關中人創新、高超的建設理念和技術,還有關中這片土地上開放、進取的文化氣度。及至唐以后,隨著生態環境日漸惡化、經濟中心東移,關中喪失了政治中心地位,日漸式微,特別是經過有明一代閉關鎖國政策,逐漸安于“四塞之固”,慣于抱殘守缺,禁錮于“城墻思維”,保守的標簽因此而來。其實細想一下,“四塞”還是那個“四塞”,是優勢還是弱點,歸根結底,在于理念。所謂“理念一新天地寬”,只要愿求新、肯求新,總能“天塹變通途”。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我們家又重新過上了安穩日子!”
- 這句贊譽,飽含著鞏某對山東省新泰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心的誠摯感激。不久前,他走進新泰市綜治中心,向工作人員連聲道謝 “謝謝你們幫我...[詳細]
- 人民法院報 2025-03-29

《經濟日報》專訪山東省委書記林武: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擔當 推動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
- [詳細]
- 經濟日報 2025-03-29

《人民日報》專訪山東省委書記林武:奮力開創民營經濟發展新局面
- [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3-29
14項重點任務錨定400億產值 山東推動陶瓷琉璃產業高質量發展
- 人民網濟南3月28日電近日,山東省工業和信息化廳等14部門聯合印發《山東省陶瓷琉璃產業傳承創新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力爭到2027年,全省...[詳細]
- 人民網山東頻道 2025-03-28
康復大學青島中心醫院為肝移植肺癌患者成功施術
- 本報訊近日,在康復大學青島中心醫院多學科的緊密協作下,經歷過肝移植手術和肺癌手術的患者鄭先生帶著康復的喜悅走出病房。今年2月,曾經...[詳細]
- 健康報 2025-03-28
四地稅務部門公布個人未申報境外收入風險核查案例
- 本報訊近日,湖北、山東、上海、浙江四地稅務部門公布個人未申報境外收入風險核查案例,提醒督促納稅人開展整改。前期,根據稅收大數據分析...[詳細]
- 中國稅務報 2025-03-28
推行所得稅申報“三步輔導法”
- 近年來,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青島片區稅務局推動“包容審慎監管和柔性執法方式”深度融入稅費管理,探索形成企業所得稅申報事前...[詳細]
- 中國稅務報 2025-03-28
信息化賦能提升監督質效
- 本報訊日前,山東省青島市清廉鄉村數字監管平臺“鄉村振興資金收益監管”板塊發出預警,顯示某區鄉村振興資金收益存在監管風險。收到提示后...[詳細]
- 中國紀檢監察報 2025-03-28
構建推動所屬商會提質增效新體系
- 為推動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大顯身手,青島市工商聯聚焦商會改革發展,通過構建“制度保障+精準培育+服務賦能”體系,推動商會提質增效。夯...[詳細]
- 中華工商時報 2025-03-28
發揮公益訴訟檢察職能作用服務鄉村全面振興
- □本報記者董凡超3月2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一批檢察公益訴訟服務鄉村振興典型案例。這些案例涉及耕地保護、農村農業文化遺產傳承、農村...[詳細]
- 法治日報 2025-03-28